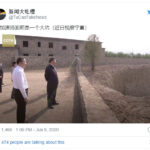夹边沟
近日,中共作协、党媒《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官方权威机构,评选中国百年名作家,正式将一贯揭露中共治下社会黑暗,但是大陆境内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
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光明日报》6月22日发表中共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吴义勤《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国百年来上百具有所谓红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建政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而莫言和他的魔幻大作却不见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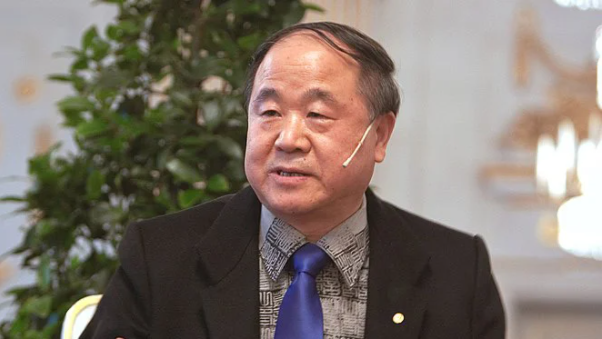
《文艺报》总编梁鸿鹰《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一文,也列出的大量红色作家和作品,莫言也榜上无名。
据中共作协吴义勤声称,中国新文学必须“讲好党的故事”。
本身是中共党员的莫言的作品被亲共文人批没有一部是歌颂所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几乎都在揭露黑暗面。
莫言曾经写道:“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能真正产生“大悲悯”(莫言《生死疲劳》)。
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莫言讲话的视频,他说: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中共央媒在评选百年名作家之际曾发表重磅文章,强调文艺为中共服务。称凡是抹黑、诋毁“中国”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被唾弃等。
不过,在百年名作家里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包括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他们揭露的是(中共篡政之前的)旧社会。
莫言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天堂蒜薹之歌》,该书反映出了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弱势和生存艰辛,同时抨击了中共政府对人的漠视和生命尊严的践踏。
1997年,莫言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大家文学奖”,获得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丰乳肥臀》赞美了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日功劳,同时没有回避敏感的斗争老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回避大饥荒饿死诸多人口的历史事实等。但该作品主旋律是赞美中共。
2011年8月,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为其“以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大陆公民。
放过莫言!给这个时代留点体面
中国离诺贝尔奖实在是太遥远了,遥远到70多年才出了两位,而日本在同样的时段里下饺子一般出现了27位,获奖的领域涉及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
建政70多年,中国政府认可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仅仅只有莫言和屠呦呦…
莫言和屠呦呦,刚好一个文学一个科学,也算填补了中国在诺贝尔奖的空白,实在是可喜可贺。
老实说我们为了获得诺贝尔奖,不是没有努力过,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见起色,文学创作一度百花齐放。有领导人认为建国已近40年,无论从国家形象、还是从文化宣传等各方面考虑中国都需要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官方当时认为中国最适合获得诺奖的作家是王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
1986年有关方面遂盛邀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博士访华,拟做一些游说工作,但马悦然博士认为沈从文先生更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并主动做了大量的推广工作。
1988年,沈从文先生第二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且被多数评委认定为当年的获奖者,可惜沈从文先生竟于当年5月10日与世长辞。马悦然博士痛心之余继续在瑞典推广中国文学作品。
又过了漫长的24年,这才有了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大陆的作家。
好不容易出了一位诺奖作家,我们珍惜了吗?
好像没有。
获奖之初就非议不断,最近更有一帮五毛对莫言发起一轮莫名其妙的疯狂撕咬,看来有些人并不珍惜这位70年才诞生一位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最近有人居心叵测翻出了2012年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一段发言,通过放大镜+显微镜的仔细研究,发现了莫言反党卖国媚洋的言论。
莫言说了什么呢?他讲了关于母亲教会他怎么做人的一个故事。
莫言说: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
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母亲的想法大抵是希望儿子不要报复一个可怜的老人,即使那个人当年被上面赋予了一点点权力时曾经肆无忌惮伤害过他们母子,那是他的错,更是那个荒谬的时代的错……
攻击莫言的大概率和攻击方方的是同一类人。他们发掘出莫言的这些言论后如获至宝。根本不懂莫言说这些话的原意,或者他们也不愿意懂,就开始断章取意对莫言进行疯狂的攻击。
有人说:莫言的文章就是抹黑中国,不然他怎么会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还有人摇头晃脑说:第一:有人看守,说明生产队还没收完,不让捡,那么莫言母子属于偷盗行为。第二:就算莫言母子偷盗,最多也是没收,不会冲上来就一巴掌,还打出血来。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说不定还沾亲带故的。再说那个年代民风淳朴,不认识的也不会下重手,除非莫言母子是屡教不改的惯犯。所以,莫言说的是要迎合西方摸黑中国的故事。
有人一针见血:莫言所说的是别有用心的捏造,试想什么季节收麦子,捡麦穗应该在什么时节?寒冬腊月有麦穗可捡吗?另外,在那个年代,麦子收割完毕,麦穗是随便捡的,有什么挨打的?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也经常组织小学生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捡麦穗,然后交给生产队。
又有人质疑:莫言是1955年生人,他所说的小时候是哪一年?拾麦穗是在什么情况下?他妈妈带他拾麦穗是什么时间段?为什么没有去生产队上工?
问题这就来了,莫言大师说的去拾麦穗,集体拾过了吗?他妈妈为何没有跟着社员们干农活去?莫言大师在获奖感言中讲这个故事(我只能称之为故事),他想表达啥意思?是批判看麦田人的凶残还是歌颂他妈妈的善良?
还有人一锤定音:莫言大师当过兵,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过。深受党和军队多年的培养,他把这份恩情放在脑后还是放在心里了?
有人说莫言作品是魔幻主义风格,我是文学的文盲,不知道他是什么风格,只知道他得了好多西方世界的奖。看过他一些文字,但是,从《丰乳肥臀》之后,一个字不看,《丰乳肥臀》 也只是看了一半儿。他的小说,只有批判,没有歌颂。一个不懂感恩人的文字,是阴暗的!
……
够了吧!请给这个时代保留一点体面。
一个号称准备复兴的民族、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至少应该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吧?至少是尊崇创作尊崇人性的吧?至少也需要一个诺奖作家装点一下盛世繁华吧?
文戈已经结束45年了,噩梦的影子还萦绕在很多受害人的心间,现在需要再用文戈的文字狱手段赤裸裸地在互联网对一个有良知的诺奖作家施行网暴吗?
世界会怎么看我们?
后代会怎么看我们?
缺少优秀的作家是一个民族的遗憾,有了而不知道珍惜就该是这个民族的耻辱了。
莫言曾经在某处留言: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 尸横遍野, 俱是农家子弟”。
仅凭此语所拥有的人文情怀,莫言就可以进入中国当代作家三甲。
搜狐文章:莫言的问题不可容忍
伴随炎热夏天而来的是批判莫言的热潮。这种群众性热潮一浪盖一浪,经久不衰;参与者为数众多,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合乎潮流,顺应民心,正向纵深推进。
“7.1”前夕, 作协秘书处吴义勤和《文艺报》主编梁鸿鹰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百年文学的红色基因》《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的文章,盛赞百年来具有红色基因的著名作家和作品,新中国建立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而 莫言和他的魔幻大作却消声匿迹不见踪影。
可以认为,文艺界的权威机构和刊物以及权威媒体,己将莫言及其作品赶出了红色作家作品之列, 因为莫言和他的作品缺少红色基因,缺少代表人民利益的因素,缺少为人民大众服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问题很严重。
第一,存心暴露社会黑暗
莫言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的创作(小说、散文、讲话等)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大部分反映的是新中国新社会的生活。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可是在 莫言的笔下这些伟大成就,这些伟大人物和先进分子,难觅踪影。
在他的作品中,环境就是悲惨世界,经历就是苦难历程,人物除了他母亲全是坏蛋。
他只写阴暗不写光明,只写落后不写先进,只写消极不写积极,只写苦难不写欢乐,只写假丑恶,不写真善美。
写阴暗面也竭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將个别说成全体,将零星说成普遍,将偶然说成必然,将临时说成长期,将少说成多,将小说成大。
在 莫言的作品中,看不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在莫言笔下,中国人民永运落后、贫穷,懦弱,没有希望,无可救药。
第二,蓄意抹黑新中国
莫言用作品暴露社会黑暗,歪曲现实生活,并非大众曲解他的魔幻作品,更不是欲加之罪,而是他自己明白无误地自白:
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
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他不写新征程、新成就,不写革命英雄,不写先进分子,不是由于生活阅历所限,不是兴趣爱好使然,而是根本不想写。他就是要暴露黑暗,社会的“坏人”。
他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经过变形、夸张、扭曲等魔幻手法改造过的“现实”,哪有什么真实性可言。
莫言暴露的“黑暗”社会是新中国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所以他暴露黑暗的目的就是抹黑中国,诋毁社会主义。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毫无顾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 贼胆包天宣扬他偷集体的麦穗、偷叔父的钢笔、偷别人的红罗卜劣迹;
他色胆包天兜售“母亲”的丰乳肥臀;他狗胆包天反噬国家和人民,丑化干部,侮辱群众,乞怜西方反华势力。
如此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的人能写出什么“人性美”?在莫言的心里和作品中只有贼性美、色性美和狗性美。
第三、发泄心中的怨恨
莫言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怨恨,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每个字节都喷射着无穷无尽的怨气,世人皆仇敌,万物尽含恨。
虽经数十年倾泻发泄,至今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莫言的怨恨来源于家庭的变故和个人的遭遇。
解放前,莫言家是富裕中农。这样的人家有自己的田地,自家人耕种,农忙时请一点短工。收成后不需向人交租,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经济较为宽裕。小孩能够上学,家庭成员略有文化。无匪患骚扰,少官吏加害,自得其乐,安然度日。
解放后经济上不会受到冲击,但社会地位不如依靠对象的贫雇农。五十年代出生的莫言从长辈处感知到这种变故,产生了失落感。
六十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粮食匮乏。莫言家有人当干部,日子可能好过一些,但挨饿难以避免,莫言受不了,记恨在心。
七一年,掌管家庭的支柱莫言的奶奶去世,原来的大家庭瓦解。这种家庭规模由大变小势力由强变弱的变故,在莫言心理上留下创伤。
对于辍学,莫言耿耿于怀,但是辍学原因只字未题。据说是因为在学校偷了别人的钢笔被老师教育,他非但不听反而骂老师。他觉得没脸在学校面对老师同学,只好辍学。尽管错在自己,但辍学让他的童年少了许多欢乐,使他感到孤独凄凉,因而怨恨社会对他不公。
进入部队后,由于文学创作思想不正被劝离,他认为这是一次耻辱。因为长得丑,同学嘲笑他,打他,连城里的文化人也嘲弄他。在他心中,人人都对他不怀好意,因此,他心中没一个好人。
莫言之所以能由一个只上过5年小学的农民成为一个作家,全靠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可 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这是因为他私心太重,只能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世界都应服从我,不能让我有丝毫不适,否则,即便你曾给我千般恩惠,我也六亲不认,睚毗必报,绝不留情。莫言是个忘恩负义极端自私的小人
第四,迎合西方反华势力需要
莫言的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开放, 西方资产阶级思潮浸入中国,崇洋媚外意识抬头。贬低、打压、抹黑新中国的逆流在暗中涌动。
这股逆流被莫言看中,如获至宝,将其跟积存在心的怨恨结合,形成了他的怨恨自由化思想。这种思想用于文学创作就是他的媚外抹黑文学。
媚外文学、抹黑文学都是违背主流民意的文学,都是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及其创作者,都将被人民大众所唾弃,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夹边沟右派噩梦:吃死人 海归科学家活活饿死
1957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将55万大陆知识份子打成右派。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就是当时关押右派的一个劳改农场。在反右斗争中,夹边沟的右派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3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夹边沟劳教农场约有3100名被打为右派的知识份子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还要忍受挨饿、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着双重的煎熬。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他们只是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而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拼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们每天仅有半斤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三年后3000人只活下来300人。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三位饿死的留美科学家
饿死的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和沈大文。这些爱国知识份子,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怀抱满腔热情回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恭的二哥)的劝说回国从事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
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
1960年冬天,傅作恭因饥饿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
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
右派吃树叶、晰蜴、兽骨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贼骨头”的生存之道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吃呕吐物和排泄物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著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死亡高峰到来 活人吃死人
1960年9月,甘肃省劳改局计划在高台县明水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著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
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11月中旬,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彰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一部记录中国右派悲惨遭遇的影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号在香港首次公开放映。导演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强调,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
这部记录片讲述1957年,50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于非命。《夹边沟祭事》在香港首映,引起热烈反响。
影片聚焦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遇难者的后事处理。在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他们当时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和反党分子等。
不过,就像文革一样,反右也成为敏感历史,艾晓明多次在夹边沟拍摄过程中遭遇当地阻拦和跟踪,并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约谈。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他指出对民族精英全面打击的反右运动,却被定义为反右扩大化,还用封堵的方式截断这段真相的留存,说到底,中共是不会承认它的错误。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艾晓明老师拍摄这个影片,用这个东西(记录片)来比照今日,让大家觉醒,我们什么都没有变,国家的体制,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社会精英的敌视,对社会思想精英的敌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在进行着,它是党性的核心部分之一。”
胡佳表示,中共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就是从反右那里开始奠定基础,直到现在,中共是不允许有独立的思考,不允许有自由的言论的。胡佳认为,60年来,反右一直持续著。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